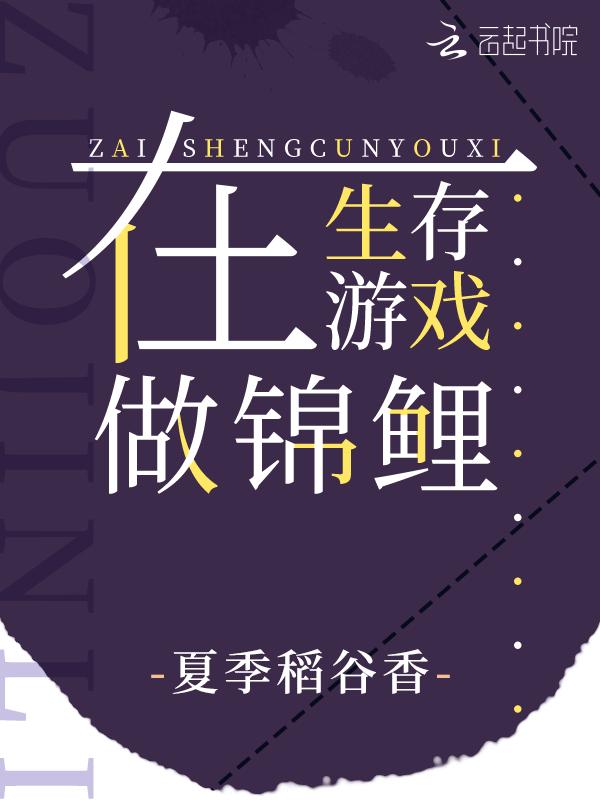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梦里南明客 > 寒衣(第1页)
寒衣(第1页)
狄玉仪抹去那滴泪,手还未曾拿开,又是一滴落在拇指。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樊循之的泪水确是比自己的要滚烫很多。
她这会儿似乎该问“哭什么”,或是做个安慰,让樊循之知道自己哄人时究竟会说什么话。可前所未有的轻快占据了她全部心神,樊循之的眼泪撼动不了分毫。
“兄长哭什么?”狄玉仪还是问了,带着无意掩盖的促狭,“因高兴还是难过?”
“都不是。”樊循之摇头,他那双眼只滚落几滴泪便作罢,可望向狄玉仪时,仍像有汪洋缩聚其中,“只是有些怕。”
怕她心口的血肉无法因自己而长,更怕它长不出来。
“袅袅放心,过会儿就好。”樊循之不提这些,只按着狄玉仪新搭上来的手不放。
“我没什么好不放心的。”狄玉仪任他握着,“该担心的是兄长才对。我只敢说努力尝试,可不保证孝期一过,立时就会嫁你。”
“没关系,袅袅遵从自己心意,顺其自然就好。”掉落崖壁的惊惧已散,可樊循之依然理不清,他是更不愿回到从前,还是更想去见长出新叶的那天。只知回过神来,他已牢牢攥住狄玉仪的手。
相印的指腹分离片刻,又各自贴上对方手掌的别处肌肤。
“嗯,顺其自然。”狄玉仪语调微微扬起,似赞同,又像质疑,惹得樊循之抬头去看。他见狄玉仪在打量两人交握的双手,以为将人捏疼,遂松了松。
狄玉仪趁此间隙往回收手,樊循之立即便又攥紧,她料到会是如此,却要装着疑惑,“拉钩不是已经结束,兄长怎还不松手?”
樊循之哪里听不出她是有意,他干咳一声,草草应着“就放”,手上却一寸不离。这次狄玉仪没告诫他不要得寸进尺,他便当不知道时辰在走。
樊循之将自己握红了脸,可越牵越不想松手。为图省力,交握的手早搁去两人之间的少许空隙,只一拳距离,因狄玉仪的手占不了什么地方,丝毫不觉局促。
狄玉仪被牵习惯,面上浅淡红云早就没了,偏樊循之像是烧着了似的。她将手贴上去一试,烫得很。虽一触即分,樊循之还是反应很大地瞪眼看她。
“兄长还是先回去冷静些吧。”狄玉仪自觉体贴,“再牵下去,你面皮都得被烫穿了。”
樊循之点头认可,但显然还是不太情愿,又磨磨蹭蹭许久。等终于起身肯走时,他又在院中一步三回头,还要求狄玉仪调转方向,好叫他回头见着的不是背影。
他说了数不清的再见,狄玉仪应了几句,他更起劲。眼见这人又有走回头路的架势,狄玉仪赶紧闭嘴不言,好歹将人送出院门。
她仍在廊下坐了好一会儿,终是没稳住送樊循之时的“淡然”,直笑个不停。笑樊循之傻,也笑自己纵容。偶尔还笑自己不自量力,可转瞬又觉,有些痴念也没什么不好。
便还是笑。
进了院的南明一头雾水,却也跟着开心起来,“看来郡主今日遇见好事了,是樊家小姐来了?”
若告诉南明,来的是樊家公子,也不知她的开心还留不留得住。过会儿再说吧,都开心久些,狄玉仪含糊应着,对人名不置可否,只笑答:“是遇见好事了。”
之后两日,除那个久得过头的牵手,两人再见,竟是无端“生疏”起来。虽也未见得安上个什么新身份,可他们心知肚明,哪里都不一样了。
生疏过了头,便是去金风堂用个饭,也能为谁先坐下谦让一番。
薛灵安摇头叹气,不知这算好进展还是坏进展。她脑中无端闪过句“儿孙自有儿孙福”,赶紧呸掉,怎将自己念老了。察觉狄玉仪关心眼神,她赶紧摆手,“没事没事,玉仪先坐,莫管樊循之。”
也罢,只要樊循之不将人惹哭,就别去瞎操心了。
樊兴南一副恨不能替儿子支招的样子,薛灵安在桌下踢了一脚,让他老实低头吃饭——这是管得住的。也有那管不住的,兴奋两天,已是憋不住了,“玉仪姊姊,你们闹掰了吗?”
薛灵安没来得及说话,狄玉仪这被问的人也没来得及答话,樊循之跟被踩了尾巴似的急眼了,“樊月瑶!瞎说什么不吉利的话呢?一边玩儿去。”
“切,充什么大人!”樊月瑶便知自己期待落空。她本决定忍气吞声,独自沉默一会儿还是气不过,“十七了!我马上十七了!”
“年节且有几个月呢。”樊循之嗤道,“这也叫马上?”
虽非马上,却也快了。隔日是十月初一,距樊月瑶除夕前日的生辰,已不足三个月。
寒衣节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