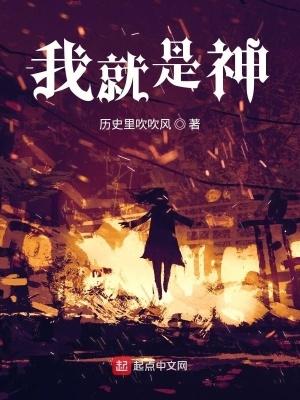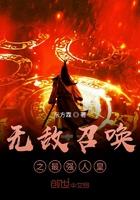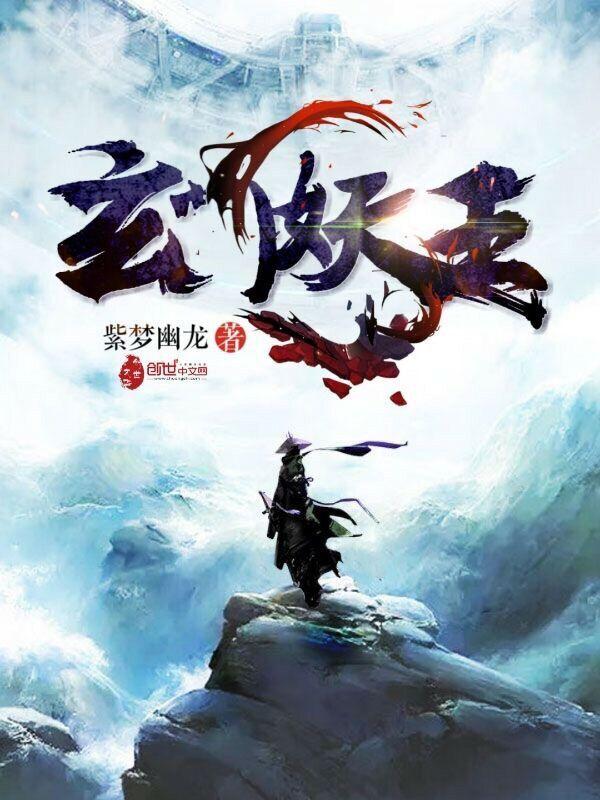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综武:我家娘子是状元 > 第533章 心剑神诀如何最快自灭满门(第2页)
第533章 心剑神诀如何最快自灭满门(第2页)
“来了。”言斋主闭目低语,“它感应到了《第十九篇》的气息。”
只见塔顶穹窿裂开一道缝隙,一道青色光柱自天而降,照在那本无名册子上。纸页无风自动,哗啦作响,最后一张空白页竟渐渐浮现出新的文字:
>“昔者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今者大道不行,群雄并起。
>吾道非隐,世人自盲。
>若有一人持灯前行,则万古长夜可破。”
字迹苍劲古拙,绝非出自今人之手。
“这不是你写的?”李公子震惊回头。
言斋主睁开眼,神色复杂:“我昨夜只写了前三句。最后这句……是它自己显化的。”
“它是活的?”广南东倒吸一口凉气。
“或许,《李兆廷典》本就是一门会进化的功法。”秦梦瑶轻声道,“它随着时代变迁、人心流转而不断生长。前十八篇是过去,第十九篇是未来,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在为它注入新的血脉。”
厉胜男挠头:“所以咱们不只是学武功,还在帮一本秘籍‘升级’?”
“准确地说,”慈航静冷冷接口,“是我们成了它的载体。”
塔内再度陷入寂静。
良久,李公子跪伏于地,郑重叩首:“弟子愿为持灯之人。”
广南东见状,也跟着跪下:“我也算一个!”
厉胜男叹口气:“行吧行吧,反正我也没处可去。”
慈航静迟疑片刻,终究单膝触地:“若此道能破迷障,我愿舍魔证道。”
秦梦瑶最后一个起身,缓步走到众人前方,转身面对他们,柔声道:“那便让我们五人,结个‘明心盟’如何?不问出身,不论过往,只问本心。从此同修共济,互为镜鉴。”
“好!”四人齐声应和。
言斋主含笑望着这一幕,轻轻拍了三下手。
刹那间,山谷内外数百盏灯笼同时亮起,宛如星河流转,照亮整座山脉。藏典塔顶的青铜铃铛再次响起,这一次,不再是孤音独奏,而是与四方庙宇、亭台、哨岗的钟磬共鸣,形成一曲恢弘浩荡的《清平调》。
山门外,已有零星身影开始攀登。
有背着药箱的老医者,有牵着孩童的妇人,有手持铁尺的捕快,也有披着斗篷的流浪武师。他们不分昼夜赶来,只为亲眼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宗门是否真的开放了。
而在山脚驿站,一名身穿粗布衣裳的年轻人正仰望着帝踏峰的方向。他肩挑两只竹筐,里面装满了新摘的茶叶与山果,额头上沁满汗水。路人问他为何这么晚还赶路,他笑道:“听说山上开始收徒讲学了,我想去问问,有没有人愿意教我识字。”
消息如野火燎原,短短两日内,已有三百余人登门求见。
程淮秀斋门前立起一块石碑,上书八个大字:“**有教无类,唯心是岸。**”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怀着善意。
第三日清晨,一名紫袍僧人踏云而来,身后跟着十二名金身罗汉,每人手持降魔杵,气势逼人。他是净念禅院八大长老之一“不动明王”释玄,专程前来质问李公子为何背弃师门,修习外道心法。
言斋主亲自迎出山门。
两人对坐松下,茶香袅袅。
“阿弥陀佛。”释玄沉声道,“贵斋开门授徒,本是善举。但令徒李兆廷曾受我禅院八年栽培,如今改投别派,岂非忘恩负义?”
言斋主抿了一口茶,淡然道:“他曾在我这里读过三天《李兆廷典》,也算我的学生。按你说,是不是他也该回你们禅院剃度?”
释玄脸色微变:“此言差矣!我禅院所传,乃是佛陀正法,岂同于区区武学秘籍?”
“哦?”言斋主抬眸,“那你告诉我,佛陀当年为何放弃王位,走入雪山苦修?是为了争权夺利,还是为了寻求解脱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