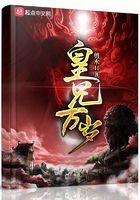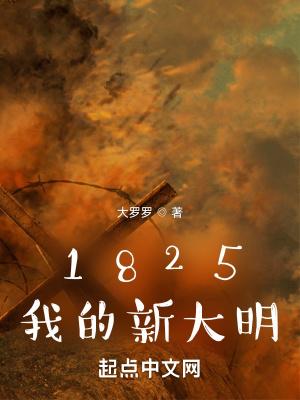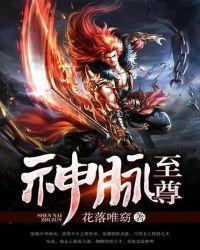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寒霜千年 > 第308章 皇帝下线(第1页)
第308章 皇帝下线(第1页)
“殿下,宋时安去了司马煜的葬礼吊唁。”
“知道了。”
太子府中,魏翊云坐在堂中的太师椅上,双手搭在扶手之上,面无表情,双瞳静若止水。
“赵毅将军居家未出,叶府君也只往返于衙门和叶府之。。。
那口钟的余音尚未散尽,沈知白却已听见远方传来新的脚步声。不是一人,而是成群,踏在湿泥上,节奏杂乱却坚定。他没有回头,只是将手稿轻轻合拢,搁回原处。他知道,这一行字不会永远停在这里??总有人会续写,哪怕用铅笔,哪怕被老师擦去。
书院外的小路上,走来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领头的是个瘦弱男孩,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通知单。他站在门口,喘着气说:“我们……我们学校要拆了。‘思想疏导中心’说我们的课堂有问题,说我们教孩子‘不服从’。”他的声音越说越低,像是怕惊动什么,又像是怕自己也变成问题。
沈知白点点头,请他们进来。孩子们围坐在石桌旁,有的低头不语,有的偷偷打量墙上那一圈钉满信纸的“钟面”。那个递通知的男孩终于鼓起勇气问:“您觉得……我们错了吗?就因为我们讨论为什么国旗必须每天升起?就因为我们问战争是不是真的能带来和平?”
“你们没做错。”沈知白缓缓道,“你们只是碰到了墙。而墙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保护人,而是为了遮住后面的东西??那些不敢让人看见的裂缝。”
他起身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破旧的练习册,封面上写着“李小满,七岁”。翻开第一页,是一行歪歪扭扭的字:“老师说太阳从东边出来,可我昨天傍晚看到它明明藏进了西山后面。难道它晚上会走路吗?”下面画了个太阳长了腿,正蹦跳着穿过树林。
“这是我女儿写的。”他说,“她八岁那年,被带走了。因为她问得太多,有人说她‘心智紊乱’。他们用梦导针清除了她的记忆,可三个月后,她在睡梦中又开始喃喃自语:‘为什么火是热的?为什么哭的时候心里会疼?’”他顿了顿,“最后他们把她送进了沉默院??那里没有书,没有提问,只有统一的呼吸节奏和每日三次的‘安心冥想’。”
孩子们听得屏息。有个小女孩小声问:“那她后来呢?”
“后来?”沈知白望着窗外,“她再也没能开口说话。但她临终前,用手指在窗玻璃上划了一道线,像一道未完成的问号。医生说是无意识抽搐。我知道,她在问:‘我还存在吗?’”
空气凝滞了一瞬。随后,那个最初递通知的男孩突然站起身,把那张纸撕成两半,扔进烛火里。火焰猛地一跳,映红了他的脸:“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学怎么问。”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有人掏出笔记本,翻到空白页;有人默默摘下校徽,放在桌上;还有一个女孩低声说:“我家楼下就有个心理稳定中心,他们每周都来检查我和妈妈有没有‘异常情绪波动’。但我昨晚梦见这栋楼塌了,底下爬出好多书,全是《疑典》。”
沈知白看着这群孩子,忽然笑了。他打开铁盒,取出那枚青铜齿轮,放在石桌上。“它不会再转动了。”他说,“真正的钟网,已经不在机器里,而在你们脑子里,在你们梦里,在你们每一次想问却又忍住的瞬间。”
他教他们第一课:如何识别“假答案”。
“当一个人回答你时,如果他先说‘所有人都知道’,那他其实不知道;如果他说‘别想那么多’,说明他自己也不敢想;如果他说‘这是规定’,那你就要问:谁定的?为什么?能不能改?”
孩子们记下这些话,像接住飘落的种子。几天后,他们在书院后院挖出一口废弃的陶缸,洗净后倒扣在地上,涂上红漆,写上两个大字:“敢问”。每逢黄昏,便有人悄悄前来,在缸底写下问题,然后迅速离开。不到半月,陶缸内外都被写满,字迹重叠如织,仿佛整座容器都在震动。
消息传开,各地青年陆续赶来。有人带着自制的“问题灯笼”,夜里点亮放飞;有人录下自己的疑问,刻成黑胶唱片,在地下电台循环播放;更有甚者,潜入国家电视台信号塔,在凌晨插播三分钟静默,只有一行滚动字幕:“你最近一次真诚提问,是什么时候?”
与此同时,镇压也在升级。
北方城市一夜之间关闭了所有公共图书馆,理由是“防止非官方知识传播”;中部某省出台新规,禁止未成年人参与任何形式的“开放式讨论”;西南边境的山区,一支巡逻队发现村民在岩壁上刻满了问题,竟动用炸药将整片山体夷平。
但每一次压制,都催生更多隐秘的回应。
被炸毁的岩壁第二年春天长出了野藤,藤蔓缠绕之处,竟自然形成类似文字的纹路;一位盲人诗人开始用指尖读这些痕迹,并将其译为诗篇,题为《山在发问》。
图书馆虽闭,可人们把书藏进棺材、埋入祖坟,清明扫墓时,子孙跪拜之余,顺手翻开一本《问源录》,低声诵读。
而那支曾执行爆破任务的士兵,退伍后在梦中反复听见岩石崩裂的声音,醒来却发现自家墙壁渗出水渍,水中浮现出一行字:“你执行命令时,想过它为何要被毁灭吗?”
最令人震惊的变化发生在教育系统内部。
一名小学教师因在课堂上让学生写“我最害怕的一件事”,被举报并停职。她在离职演讲中说:“我让他们写恐惧,是因为我发现,现在的孩子连‘害怕’都不敢承认。他们以为坚强就是不说痛,成熟就是不提问。可如果连痛感都麻木了,还谈什么成长?”
演讲视频悄然流传,引发连锁效应。越来越多教师开始在教案夹层藏入“问题卡片”,表面是算术题,背面却是哲学思辨;美术课上,学生被鼓励画“看不见的东西”??于是出现了大量描绘“沉默”、“遗忘”与“被删除的记忆”的作品。
就在局势愈演愈烈之际,乌溪河畔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
那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身穿普通工装,手中提着一只老旧录音机。他找到沈知白,递上一盘磁带,说:“我是国家记忆管理局的档案员。我们负责销毁‘有害思想记录’。但这盘带子……我没法删。”
磁带上标记着编号:X-9372,分类为“高危梦境残留”。
据档案记载,这段录音来自一位已故科学家的临终脑波监测数据。机器本应自动清除所有非标准思维模式,可这段信号始终无法格式化,反而在每次尝试删除时,生成新的音频片段。
沈知白接过磁带,放入录音机。
起初是杂音,接着是一段断续的哼唱,旋律古老,似曾相识。然后,一个微弱的声音响起,像是从极深的地底传来:
>“……种进土壤……种子不死……破土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