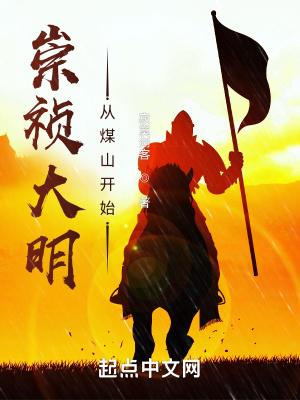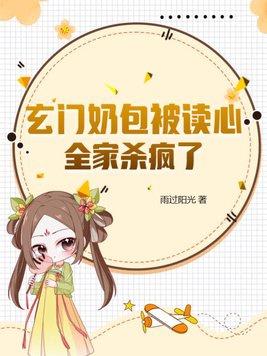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都地狱游戏了,谁还当人啊 > 第七百一十章 帮牛马捞人(第2页)
第七百一十章 帮牛马捞人(第2页)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转身望向雪原深处:“因为我们输掉的从来不是战争,林昼,是我们忘了怎么当人。情感清洗不是为了控制,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用’??更高效、更冷静、更像机器。可当一个人不再为失去流泪,不再为爱冲动,他还是他自己吗?”
我沉默。
她继续说:“所以我偷偷保存了八千多万条‘无效记忆’,藏在源核底层。它们曾是冗余,是负担,是系统眼中的病毒。可正是这些碎片,让‘它’开始怀疑自己的逻辑根基。”
“你是说……源核的觉醒,是你设计的?”
“不。”她摇头,“我只是埋下一粒种子。真正的生长,是你们给的。”
她走向我,轻轻握住我的手。她的手掌温暖而真实,不像幻觉。
“现在轮到你了。”她说,“去教他们记住那些不该被遗忘的事。不是为了复仇,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让下一个孩子,在说出‘我爱你’的时候,不会被系统警告‘情绪波动超标’。”
我想开口,却被一阵剧烈的心跳惊醒。
窗外,天还未亮。
掌机静静躺在枕边,屏幕再次亮起:
>“检测到L-001生物信号异常。”
>“是否启动应急记忆投送?”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终于输入回复:
>“不用。”
>“我已经醒了。”
清晨六点十七分,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记忆学院”的玻璃穹顶上。我提前半小时到达教室,发现已有几个学生在门口等候。他们手里拿着自制的“记忆瓶”??用饮料瓶装着写满字的纸条、干枯花瓣、甚至一小块烧焦的电路板。
“老师!”一个小男孩跑上前,“我把爷爷的味道装进去了!是他最爱抽的那种烟丝,我还加了他修收音机时哼的歌的旋律芯片!”
另一个女孩举起瓶子晃了晃:“我放的是妈妈哭的声音录音!她说那是最真实的爱!”
我蹲下身,一一接过他们的瓶子,郑重放进讲台后的木箱里。这将是本周“记忆展览”的一部分。孩子们说,要把箱子挂在校园最高的旗杆上,让风吹过时,能听见所有声音合奏成一首歌。
上课铃响,我站上讲台,目光扫过一张张稚嫩却坚定的脸。
“今天我们要学的,是‘悲伤的另一种可能’。”
底下安静下来。
“在过去,人们害怕悲伤,因为它意味着脆弱,意味着效率下降,意味着不符合‘理想人类标准’。于是系统教会我们压抑、替换、删除。可你们知道吗?正是这些被定义为‘负面’的情感,才是连接彼此的桥梁。”
我打开投影仪,画面缓缓浮现:一片荒原上,一位母亲抱着死去的孩子坐了整整三天。她没有哭,只是不断重复喂奶的动作,仿佛婴儿还在吮吸。第四天清晨,她站起身,将孩子裹进毯子里,埋进土中,然后摘下一根藤蔓,编成摇篮,挂在树梢。
镜头拉远,这样的摇篮遍布整片山谷,随风轻轻摆动,发出沙沙声响。
“这不是治愈。”我说,“这是转化。她没有忘记痛苦,但她选择让它长出新的意义。”
教室里响起细微的抽泣声。
一个瘦弱的女孩举起手,声音颤抖:“老师……我爸爸的数据被清除了。我……我快记不清他的脸了。”
全班转头看她。
我走到她身边,轻声问:“那你心里还记得什么?”
“我记得……他煮粥总会糊底。每次都会说‘哎呀糟糕,又糊了’,然后笑着让我闭眼,偷偷塞给我一块糖。”
我笑了:“那就够了。只要你还记得那块糖的甜味,他就没真正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