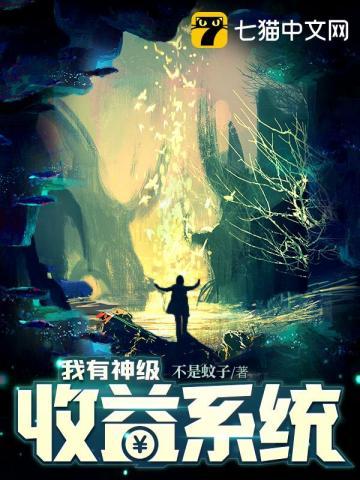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4章 大皇子周苍(第1页)
第464章 大皇子周苍(第1页)
庭院中依旧寂静,但每个人的心中都掀起了惊涛骇浪。
谁也没想到,执宰天下的首辅大人,竟有这样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更想不到他会当众剖白这段过往。几个跪在前排的官员不自觉地交换着眼神,都在对方眼中看到了同样的震惊。
黄千浒的目光缓缓扫过众人,声音沉稳如古井:“无论是曾经那个七品县令,还是如今身为内阁首辅,我黄千浒的初衷始终没变。我想为天下百姓做点事情,哪怕因此背负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他微微停顿,目。。。。。。
雪落无声,边关的冬夜总是来得格外早。归语村外那条由碎石铺就的小径已被积雪覆盖,唯有万忆塔前的忆河仍泛着幽光,如一条游动在黑暗中的碧色长蛇。小石头披着旧棉袄坐在塔下,手中捧着一卷新到的《凡人志》抄本,纸页泛黄,墨迹斑驳,是西南驿一位盲眼老匠人口述、其孙代笔所录。讲述的是陈七曾在暴雨中为护桥桩,独自守了三昼夜,期间靠啃树皮维生的事。
她读得很慢,一字一句都像在咀嚼岁月的味道。
风从山口吹来,带着铁锈与冻土的气息。远处传来脚步声,踏雪而行,节奏稳健,像是某种久别重逢的暗号。小石头没有抬头,只轻声道:“你回来了。”
李守站在十步之外,肩头落满雪花,脸上皱纹更深了,鬓角全白,但眼神依旧清亮。他将背上的包袱放下,拍了拍身上的雪,声音低哑:“今年比往年晚了些。西域下了百年不遇的大雪,有几段古道被埋得严严实实,我一路刨着走过来的。”
小石头合上书卷,望着他:“你还是不肯停下?”
“停不下。”他笑了笑,“路没断,我就不能停。况且……还有人等着听故事呢。”
他说着,从包袱里取出一本用油布裹得严实的册子,递过去。封皮上四个字??《守路日记?拾贰》。
“这是第十二本了。”小石头接过,指尖触到纸面时微微颤抖,“你每年带回来一本,十年不曾间断。”
“不止十年。”李守盘腿坐下,从怀中摸出一只扁铜壶,喝了一口烈酒,喉结滚动,“我在敦煌一个破庙里还藏了三本,等哪天走不动了,就让人一并送来。我不想让这些事,随我一起烂在荒野。”
小石头翻开新册,第一篇写的是永和十三年春,陈七率残队修复“断魂岭”栈道的事。那时朝廷已撤资多年,百姓避之如瘟疫,唯恐沾上修路的苦役。可陈七仍带着仅剩的九名队员,在悬崖绝壁间凿石穿木,以藤索吊身,悬空作业。一日狂风骤起,一名队员失足坠崖,尸骨无存。众人悲恸欲绝,欲返程归乡。陈七却跪在崖边,对着虚空磕了三个响头,说:“你们要走,我不拦。但我得留下。这条路若不通,他们明年运粮还是会摔死人。”
最终,八人离去,一人留下。
那一段路,是他一个人修完的。
小石头看得泪流满面,手指紧紧攥住书页边缘。“你说过,要讲他的软弱、他的痛楚……可这样的坚持,已经超出了凡人的极限。”
“所以他不是神。”李守低声说,“他是把自己逼成了非人的人。你以为他不怕死?怕。但他更怕辜负。怕那些信他的人,最后发现他不过是个逃兵。”
夜深了,雪越下越大。两人沉默良久,唯有忆河微光映照着彼此苍老的脸庞。
忽然,小石头问:“你还记得阿音缝的最后一件袍子吗?就是挂在碑旁那片蓝布。”
“记得。”李守点头,“每年清明,我都去那儿看看。风吹久了,布也褪色了,可颜色还在,像海,也像花。”
“去年冬天,有个小女孩偷拿了那块布,说是想做裙子。”小石头苦笑,“我本想责骂她,可她说:‘老师,我想穿着它长大,将来也要讲那个拿铲子的人的故事。’”
李守怔住,随即笑出声,眼角泛起水光。“好孩子啊……阿音要是听见,一定会很高兴。”
“我把布送给她了。”小石头轻声道,“告诉她,这不是遗物,是火种。只要有人愿意穿它、讲它、信它,就永远烧不灭。”
次日清晨,雪停了。忆学馆的钟声响起,悠远绵长。学生们陆续赶来,听说李守归来,纷纷围聚在万忆塔前。他们中有不少人是听着《凡人志》长大的,把陈七当作童年梦里的影子,真实却又遥远。
一个少年怯生生地举手:“李先生,您说陈七不是英雄,可他做的事,谁能做到?我们读书人都说,这才是真正的圣贤。”
李守摇头,目光扫过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圣贤是后人封的,他自己从没这么想过。你们知道他在临终前最惦记什么吗?不是功名,不是青史留名,而是??他问柳芸:‘阿音有没有收到我托人捎回去的那包莲籽?’”
众人静默。
“他说,家乡没见过蓝莲花,他想让她看看春天的样子。”李守声音哽咽,“可那包种子,半路被人抢了当柴火烧了。他到死都不知道。”
少年低下头,不再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