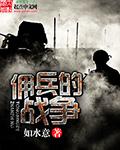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4章 大皇子周苍(第2页)
第464章 大皇子周苍(第2页)
这时,小石头站起身,缓缓走向碑前。她取出昨夜整理好的《凡人志?拾壹》,轻轻放入陶罐,重新封存,埋入土中。然后转身,对众弟子道:
“今天我要教你们最后一课。”
所有人肃然起立。
“记住,传承不是复制,而是延续。你们不必成为陈七,也不必模仿他扛铁铲、翻雪山。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当别人遗忘时,你们选择记得;当别人粉饰时,你们选择真实;当别人说‘这世道就这样’的时候,你们还能说出‘可不该这样’。”
她顿了顿,目光如炬。
“这就够了。”
话音落下,数十名弟子依次上前,在碑前放下自己的物件:一支用尽的炭笔、一双磨破的草鞋、一封写给远方亲人的信??信中提及自己志愿加入驿路巡查队。这些都是他们生命中最真实的印记。
李守默默看着,终于也走上前,将此次带来的《守路日记?拾贰》放在碑顶,任风翻动书页。
“我又写完了。”他对虚空说道,“你要是听得见,就知道,这条路,还有人在走。”
数日后,李守再次启程。这一次,他没有带走干粮,也没有要地图。只是背着那把旧铁铲,拄着一根榆木拐杖,一步一步走向西北方向。
小石头没有送他到村口,只站在万忆塔前,遥遥目送。
风起,蓝布幡飘扬,仿佛招手作别。
三个月后,东南沿海学堂的年轻教习收到一封信,信封上无名无姓,只画了一朵简笔蓝莲。拆开一看,是一份誊抄的《守路日记?拾贰》全文,附言寥寥数字:
>“请传下去。不必署我名。”
教习沉默良久,将信贴在教室墙上,召集所有学生诵读。孩子们齐声朗读那段关于“断魂岭”的记载,声音清脆如铃,穿透海风。
而在长安修史局,那位藏有《野闻录?补遗》的年轻史官已被擢升为主笔。他在编纂新版《民德卷》时,力排众议,增补一条新规:
>“凡为民赴难、守诺至死者,不论出身贵贱、职位高低,皆入‘守诺者’名录,世代铭记。”
同僚讥讽他迂腐,他只淡然一笑:“有些人活着时没人记得,死后若再无人提,那就真死了。我写一笔,至少让他们多活一天。”
与此同时,西域荒原之上,一座废弃烽燧遗址中,几个牧民的孩子发现了半截埋在沙里的木牌,上面依稀可见刻痕:“此路通归语,行者勿忘灯。”
年长些的孩子认得这几个字,是忆学馆教过的。他们找来石块堆成标记,并在旁边插了一根削尖的树枝,挂上一块碎布条。
“我们要不要告诉大人?”一个小女孩问。
“不用。”男孩摇头,“等明年,还会有人路过。他们会看见,会记住,会继续传下去。”
果然,半年后,一名驿卒途经此地,见到标记,掏出随身携带的炭笔,在木牌背面添了一句:
>“今岁三月,西风驿张六至此,知路未断。”
他又从怀里取出一小包干粮,放在石堆旁,喃喃道:“不知是谁留下的规矩,走过这条路的人,都要给后来者留点东西。哪怕一口水,也算接上了气。”
这一习惯,早已悄然蔓延至全国十九驿。无论是老兵、商旅、工匠还是学子,只要踏上这条曾由陈七及其同袍一寸寸开辟出来的道路,都会自觉留下些许物品:一把米、一束线、一页笔记、一首诗。这些东西或许微不足道,却串联起千里之外人心之间的温度。
又三年,春寒料峭,蓝莲花尚未盛开。小石头病倒了。
她躺在老屋改建的忆学馆厢房里,窗外是那片熟悉的山坡。床头放着一枚铜扣,正是当年李守交给她的那一枚。每日清晨,都有学生来为她读一段《凡人志》,或是一封来自远方的读者来信。
其中有一封,来自北境极寒之地的一位戍边校尉。信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