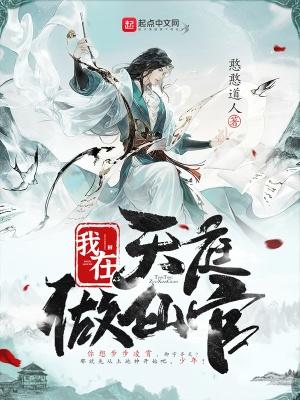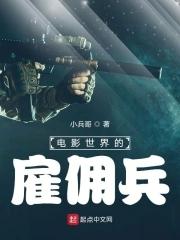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3页)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3页)
>
>可正是这份相信,让那些冰冷的夜晚有了温度。”
史官读罢,泪流满面。他当即奏请皇帝,请求在“守诺者”名录中增补一项女性专录,并提议将每年春分定为“守诺纪念日”,全国鸣钟报晓,诵读院训。
朝中仍有反对之声,称此举“过于民间,不合礼制”。他冷笑反驳:“若连一个愿意等丈夫回家的女人也不配被铭记,那我们供奉的礼制,不过是粉饰太平的空壳罢了!”
最终,圣旨准奏。
同年秋天,守诺书院迎来百年庆典。来自全国十九驿的代表齐聚一堂,带来各地民众亲手编织的蓝布长卷,长达百丈,上绣万千名字??有已知的守路者,也有无名之人。长卷徐徐展开,覆盖整个广场,宛如一条流动的蓝莲花河。
陆沉作为学生代表发言,他说:
“我们不必复制过去,但我们必须拒绝遗忘。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因为某个人伟大,而是因为我们终于明白??
**平凡人也能点亮黑夜**。
只要他还愿意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摆在路上;
只要她还肯为陌生人留下一口水、一盏灯;
只要还有孩子指着蓝莲花说‘我也要讲那个拿铲子的人的故事’??
那么,这条路,就永远不会断。”
庆典结束当晚,天空突现异象:一颗流星划破长空,坠落在西北群山之间。当地牧民称,次日清晨前往查看,竟在陨石坑边发现一座新坟,坟前铁铲依旧,红绳未朽,旁边石块堆成标记,上面用炭笔写着:
>“路尚通,吾暂歇。”
无人知晓是谁所立,亦不知是否真有其坟。但自此以后,每逢春至,那处山谷总会开出一片蓝莲花,洁白花瓣中心晕着淡淡幽蓝,香气清远,经月不散。
有人说,那是阿音终于看到了家乡的春天。
也有人说,那是陈七与李守,在另一个世界并肩巡路,累了,便坐下歇息片刻。
更多的人相信??
那不是终点,是起点。
就像最初那一铲泥土落下时那样。
就像千万次有人选择“再走一趟”时那样。
它不在传说里,不在碑文中,不在庙堂之上。
它在每一次低头拾起责任的瞬间,
在每一句“我还记得”的低语中,
在每一个明知前路艰险,却依然迈出脚步的身影里。
它在路上。
它在人间。
它,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