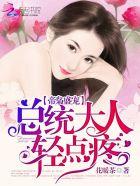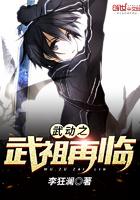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2页)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2页)
>“若修路是为了敛财,不如让它永远断着。”
此信激怒权贵,遂下令封锁归语村,禁止任何人出入,更不准再提“陈七”之名。然就在当夜,万忆塔前忽然燃起九盏灯,据村民回忆,那是九位曾与陈七共事的老驿卒,各自点燃一盏,静坐整夜。翌日,他们相继失踪,有人说他们去了西域,有人说他们隐入深山,但谁都知道??他们是去继续修路了。
《拾陆》的作者写道:
>“我找到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叫赵五,原是陈七副手。他如今住在沙漠边缘一间土屋里,双目失明,双手枯如树根。我问他为何不回乡养老,他笑着说:‘我答应过他,每年春天要去看看那几段最险的路有没有塌。我没忘。’
>
>我陪他走了三天,把他背到一处悬崖边。那里有一块歪斜的石碑,上面字迹模糊,依稀可辨:‘此处慎行,风急路窄。’
>
>他伸手摸了许久,忽然流泪:‘这不是官府立的……是我们自己刻的。那时候没工具,拿铁铲背面一点点凿出来的。’
>
>那一刻我才明白,真正的路,从来不只是石头和木头铺成的。它是承诺,是记忆,是哪怕明知无人看见,也要刻下一刀的决心。”
宣读完毕,书院内外鸦雀无声。
良久,陆沉起身,走向殿中画像,深深一拜。
当晚,他写了一封信,寄往西南故乡:
>“娘,我见到了父亲走过的路。
>它还在。
>而且,有人一直在修。”
与此同时,在极西之地,一座孤零零的烽燧遗址旁,一场沙暴刚刚过去。几名商旅歇息于此,清点货物时发现,原本绑在骆驼背上的水囊少了一个。正欲责骂赶驼人,却见远处沙丘上插着一根木棍,挂着破布,底下压着一块石板,上面刻着几行字:
>“此处无水,前行十里有泉。
>前人所留水囊已被取用,恕未归还。
>后继者,请补一袋。”
众人面面相觑,随即默然解下自己的水囊,留下一袋清水,又添了几块干饼。
其中一人掏出炭笔,在石板背面写下:
>“今岁四月,陇右商队至此,知恩当续。”
他们不知道,这块石板,最早是由李守亲手所立。几十年来,历经风沙掩埋、战火焚烧,一次次被人挖出、重刻、补写,已成为丝绸之路上最古老的“活碑”。
而在长安修史局,那位曾力主设立“守诺者”名录的主笔史官,近日收到一封密函。拆开一看,竟是当年被焚毁的《野闻录?补遗》残卷复印件,附带一份手稿,标题为《阿音传》。
原来,多年之前,李守曾在敦煌某破庙中,遇见一位年迈绣娘。她说自己年轻时曾在归语村外见过一个女子,每日坐在河边缝衣,口中哼着一首无人听懂的小调。她曾受其恩惠,得一件御寒棉袍,袍角绣着一朵蓝莲。后来听说那女子叫阿音,便一直记着。
这位绣娘花了三十年,凭记忆复原了阿音所有的针法与纹样,并收集民间口述,写下这份《阿音传》。她在文末写道:
>“世人皆知陈七守路,却不知有一女子,用十年光阴为他缝制冬衣二十三件,夏衫十七套,鞋袜无数。她不曾踏上那条路,却把一生线头,全都系在了他的脚步上。
>
>她不是英雄,也不是烈女。她只是一个相信‘他会回来’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