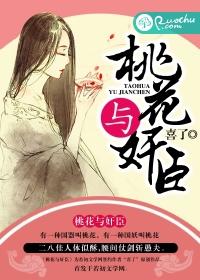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被病娇小狗缠上了 > 110120(第4页)
110120(第4页)
处似乎软了一下。
她伸出手,指尖轻轻捏了捏他发烫的耳垂,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叹息,低语道:“真是可怜的小狗。”
季斯允只记得自己最后一点不安和惶恐也在她温暖的怀抱和这声叹息中消散了。
混混沌沌的脑袋意识沉沉,她温柔的嗓音忽远忽近听得不太真切,在她的怀里,季斯允紧绷的神经彻底放松,最终安心地陷入了黑甜的梦乡。
回忆至此,那一丝微弱的、带着羞赧的喜悦再次悄悄爬上他苍白的心头。
她好像……没有讨厌他,即便知道他做了那种事,还愿意用那样温柔的语气安抚因为愧疚而不停落泪的他。
季斯允怀着一种虔诚的的心情,小心翼翼缓缓转过身,想要确认那并非梦境,想要再次看到那个给予他短暂安宁的怀抱。
然而,身侧的位置空空如也。
冰冷的床单,平整的枕头,没有一丝余温。
季斯允脸上的那点血色和刚刚升起的微弱光彩,瞬间褪得干干净净,比之前更加惨白。
这一幕,熟悉得可怕。
曾经,他也是这样从混乱和短暂的温暖中醒来,满怀卑微的期待,却看到同样空荡冰冷的床铺。
然后,等待他的不是温存,而是刻骨的羞辱——被人当作出来卖的,塞了张支票,像打发垃圾一样让他“滚远点”,甚至连出面处理的人都不是她本人,仿佛他只是她不小心沾染上、需要立刻清理掉的污秽。
那个困扰他多年、如同梦魇般的心魔,再次张开了巨口,将他吞噬。
季斯允只觉得天旋地转。
所有的理智和刚刚建立起的微弱安全感瞬间崩塌。他什么也顾不上了,甚至不敢去想她去了哪里,是不是又一次……嫌弃地将他丢开。
季斯允猛地从床上弹起,手脚冰凉发颤,胡乱地抓起散落在地上的、皱巴巴的衣物,迅速地套在身上。
他甚至不敢回头再看一眼那张凌乱却空荡的大床,像身后有恶鬼追赶一般,踉跄着冲出酒店房间,砰地一声带上了门,将昨夜那短暂虚幻的温柔彻底关在了身后。
就在季斯允仓皇逃离后没多久,套房内另一间卧室的门被轻轻推开。
宋攸宁已经换好了衣服,神清气爽,一边讲着电话一边走出来:“……嗯,知道了,叫他先盯着,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她握着手机,抬眼看向主卧室的方向,想着那个哭包不知道醒了没有,下意识放轻脚步走向主卧方向。
电话那头还在说着话,宋攸宁的目光落在主卧紧闭的门上,心思却有些飘远。
昨晚,她原本是打定主意要好好教训他一番,让他彻底记住擅自欺骗她、躲着她的后果。可后来……看他哭得那样凄惨,缩在床角像只被遗弃的小动物,心肠终究还是软了下来。
到底还是年纪小。她心想,从小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没人好好教他,行事偏激了些,长歪了点,似乎也情有可原。
既然该受的惊吓和教训也受了,只要他从此以后乖乖的,不再犯浑,她也不是不能给他机会。
人嘛,总要允许犯点小错的。
所以后来,她才收敛了所有脾气,耐着性子去安抚他,替他擦眼泪,把他抱在怀里轻声细语地哄。
也不知道他昨晚哭得迷迷糊糊的,有没有听进去她后来说的那些软话?有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她这么想着,手指已经推开了主卧室的门,同时对着电话那头应道:“嗯,继续说……”
话音在她看清房间景象的瞬间,戛然而止。
房间里,窗帘依旧拉着,光线昏暗,那张凌乱的大床上空空如也。
宋攸宁握着手机的手指立刻收紧,她甚至没意识到电话还没挂断,目光带着一丝不敢置信,再三扫过空荡荡的床铺,随即脚步略显急促地转向浴室,一把推开门——同样空无一人。
他不在房间里,也不在浴室。
竟然……走了?
几秒钟的死寂后,宋攸宁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从错愕到难以置信,最后,化作一声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荒谬意味的冷笑。
“呵。”
她竟然被季斯允给气笑了。
电话那头,高菁汇报完季斯允父亲近期的情况——因欠下巨额赌债被追讨,四处躲藏,这些年一直没放弃寻找季斯允。
倒不是因为他突然良心发现想要找回那份亲情,而是想找到儿子替他还债,甚至动了拿儿子抵债的肮脏念头。
这也正是季斯允多年来一直如同惊弓之鸟,不敢公开露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