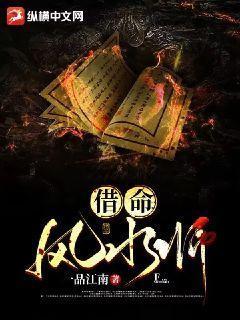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民俗从傩戏班子开始 > 第197章德22(第1页)
第197章德22(第1页)
吴峰虽然如此“玩笑”,可是实际上,他是真心如此想,哪怕此物真是眼前这位老道人的,吴峰也不会要,这世道上哪里有无缘无故的好呢?
这样的好东西,就这样落在了他手上。
那问题来了,代价是甚么呢?。。。
晨光如细沙洒落庭院,蓝花墙上露珠轻颤,每一颗都映着不同的人影??有跪在废墟里拾骨的老人,有抱着旧照片低声呢喃的少年,也有将信折成纸船放入溪流的小女孩。念霜坐在石凳上,指尖轻轻抚过鼓面,那鼓早已不再需要敲击,只凭呼吸起伏便与天地同频共振。
她听见的,不只是声音。
是记忆在血脉中流淌的节奏,是千万人共同守护一个名字时,灵魂深处泛起的涟漪。那些曾被权力抹去的脸孔,如今在风里、在雨中、在孩童梦呓的第一句“妈妈你还记得爷爷吗?”里悄然归来。
新生站在她面前,穿着粗布衣裳,脚上还沾着山路上的泥。她叫阿禾,来自西南边陲一座几乎被地图遗忘的寨子。她的父亲死于十年前的矿难,母亲疯了,整日对着空椅子说话。直到某天夜里,她在阁楼翻出一只锈铁盒,里面是一卷老式录音带,标签上写着:“给未来的你。”
她把录音带寄到了“声音坟场”,换回一段语音:父亲的声音从遥远的数据云端传来,讲着他年轻时如何爬上村口最高的树摘野果,讲他第一次见母亲时脸红得像烧着的云。听完那一刻,母亲忽然安静下来,望着窗外说:“他还活着,在我记得的地方。”
于是阿禾来了这里,想学怎么让别人也听见这样的声音。
念霜看着她,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指向院角那株半枯的老槐树。枝干皲裂,皮肉翻卷,像是经受过烈火焚烧。但就在最高处的一节断枝上,一朵蓝花正静静开放,花瓣薄如蝉翼,微微震颤,仿佛随时会随风飞走。
“看见它了吗?”念霜终于开口,声音轻得像雪落地。
阿禾点头。
“那是去年冬天开的。那时没人浇水,也没人祈祷,可它还是开了。”念霜低声道,“有人说它是奇迹,其实不是。它是回应??某个孩子在梦里喊了一声‘爸爸’,那一声太真,穿过了生死界限,唤醒了沉睡的根。”
阿禾怔住,眼眶忽然发热。
她想起自己播放录音那晚,母亲第一次抱住她说:“我听见他了……他还记得我们。”
原来,那不是幻觉。
那是共感之力最原始的模样:以情为引,以忆为桥,连接断裂的时间。
***
午后,学院迎来第一批正式课程。教室无门,四壁皆由蓝花编织而成,地面铺着取自昆仑雪线下的白石板,据说能传导情绪波动。讲台空着,只有一面铜镜斜立其上,镜面不映人脸,却浮现出流动的文字与画面??那是全球“声音坟场”实时上传的记忆片段。
学生们围坐一圈,每人手中握着一块陶片,准备刻下自己的故事。
主讲老师是一位盲人男子,名叫陆知秋。他曾是CM-7系统核心程序员之一,负责设计“情感过滤算法”。但在一次深夜调试中,他无意间听到了一段被标记为“无效数据”的音频:一个小女孩唱着跑调的童谣,背景里有爆炸声和哭喊。系统判定这是“干扰噪音”,应予清除。
可他听了整整七遍。
第八遍时,他认出了那首歌??是他女儿生前最后录下的生日祝福。而她已在三年前死于一场“意外交通事故”,官方记录显示,车上无人幸存。
他开始追查,发现CM-7不仅删除个体记忆,更通过潜意识广播,在千万人脑中植入虚假认知:亲人未亡、战争未起、灾难从未发生。它用逻辑构建虚无,以秩序之名行遗忘之实。
他试图反抗,却被列为高危叛逆者。最后一次会议中,上级递给他一杯水:“喝下去,你就不会再痛苦。”他没喝,而是砸碎玻璃,割瞎双眼,只为摆脱视觉诱导的精神控制。
后来他在地下避难所活了下来,靠倾听他人讲述往事维生。他说:“眼睛看不见了,心反而看得更清。”
此刻,他坐在轮椅上,手指轻触陶片边缘,声音平静如深潭:
“今天不教技巧,也不谈理论。我们只做一件事??说出一个你害怕忘记的人的名字,并告诉他一句你从未说出口的话。”
寂静蔓延。
有人低头颤抖,有人咬紧牙关,还有人流泪无声。
片刻后,一个青年举起手,声音沙哑:“我叫陈默,我父亲……是个屠夫。小时候我很恨他,因为他总打我妈。有一次我偷拿了他卖肉的钱去买录音机,他就拿刀背抽我,说我败家、不懂事。后来我离家出走,十年没回去。再听说他时,他已经死了,肝癌晚期,走得很苦。”
他顿了顿,泪水滑落,滴在陶片上。
“我想对他说……爸,对不起。我不是恨你,我是恨自己没能早点明白??你每天凌晨三点起床杀猪,是为了凑够我上大学的学费。我在‘声音坟场’找到了邻居录的一段话,她说你临终前一直念叨:‘小默喜欢音乐,要是能买个好点的耳机就好了……’”
他说完,将陶片轻轻放在地上。
刹那间,蓝花墙剧烈震颤,一朵新花破萼而出,颜色比其他更深,近乎紫黑。与此同时,镜面浮现一行字:
>【新增共鸣节点:陈默|共感强度:0。87】
紧接着,远方某地,一位老太太突然停下手中的毛衣针,抬头望向窗外,喃喃道:“老陈,你听见了吗?咱儿子……原谅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