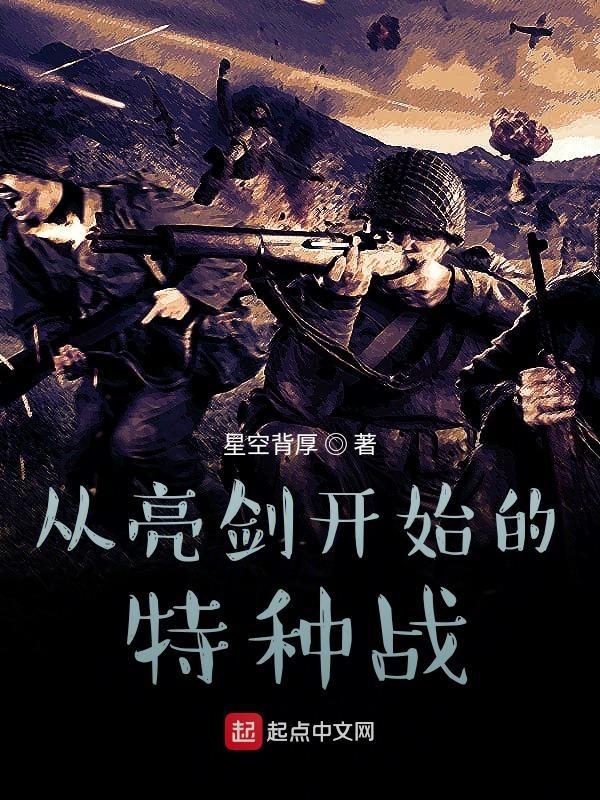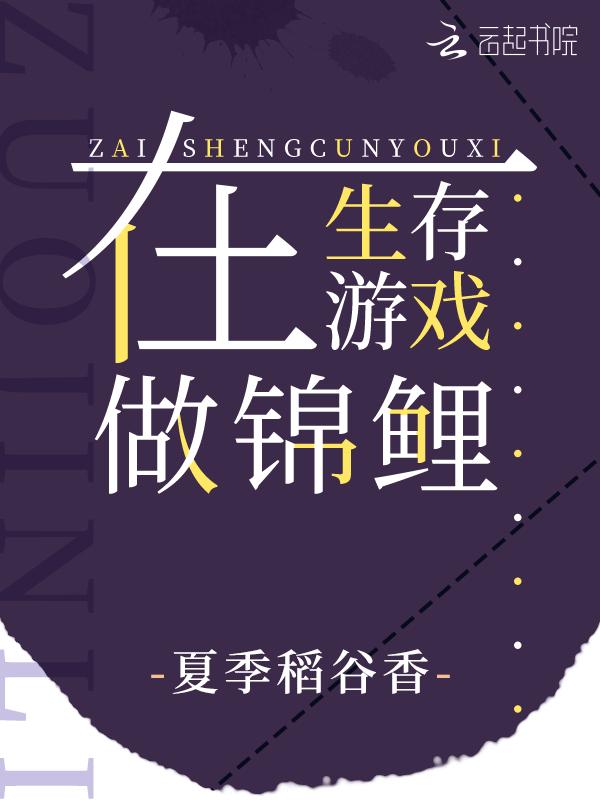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跋扈二小姐平步青云 > 第四十一章 永巷(第2页)
第四十一章 永巷(第2页)
转向青绿才要说话,青绿摆摆手,示意内监离开。
出了房门,青绿对内监道:“这些房门你先别锁上,回头我与她们聊几句。”
内监讨好道:“主簿随意,其实这门上不上锁都无甚大碍,别说犯妇出不了永巷,便算出了永巷也出不了宫门,主簿走后我再进来锁上便是。”
青绿居高临下地点点头。
内监又小心翼翼地问:“永巷出了什么岔子么?这么晚了,主簿还亲自进来。”
青绿轻描淡写道:“与内监无关,只是有件差事恰好与十七号有些瓜葛,既然进来了,也顺便了解一下别的,你想知道?”
内监忙摆手:“不,卑职不敢,不是永巷的问题便好,我可都是尽心尽责地管着这一亩三分地。”
青绿点头:“这个我知道。”
将到巷子尽头,内监开了房门喊道:“七竹。”
青绿就着内监举着的灯笼,看见一张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清瘦长脸,双眼眼距较宽,鼻梁扁平,正是清明节在夕颜殿见过的妇人。
妇人神情冷漠地抬起眼眸看了一眼青绿。
查验完毕,青绿与内监掉头往回走,在十二号房门前,青绿对内监道:“我与十二号犯妇说几句话。”
内监识相地点头道:“明白。”
青绿目送他出去关了大门,转身进了十二号牢房,简单问了里面关着的一名妇人有关吃住条件的问题后便退了出来,此举是障眼法,她不想让内监知道她单独去见了七竹。
出了十二号,青绿看看关紧的大门,掉头快步走到七竹所在的牢房,轻轻推门而入。
她手上的灯笼照亮了这间不过巴掌大的陋室,目力所及只有一张仅容一人躺下的简陋木床,床头一角堆放着几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裳,床尾是单薄的被褥,中间摆放着些女工针黹。
七竹静静靠床沿站着,神情木然。
不知从哪个墙缝透进来的风吹得青绿打了一个哆嗦。
青绿轻声唤道:“七竹嬷嬷。”
七竹平静道:“我记得姑娘。”
青绿将房门掩上,在门旁静听了一会,靠近七竹道:“我是兰台主簿凡青绿,此处不能待得太久,只问嬷嬷几句话,望如实告之。”
七竹未置可否,眼神中带着高度戒备。
青绿不作过多解释,直截了当道:“嬷嬷是因为何事进的永巷?”
七竹眼中闪过一丝疑虑,沉思片刻,轻声道:“因为一件礼服。椒房殿陈尚衣将皇后准备在先蚕礼祭祀时穿的礼服交给我,说礼服存了一些时日,有些气味,嘱我务必亲自动手清洗干净。”
皇宫每年仲春时节都要举办籍田礼及先蚕礼。籍田礼,由皇帝亲自下农田推犁插秧以示亲耕,然后行祭祀大典;对应的先蚕礼,则由皇后率后宫妃嫔及公卿列侯的夫人,到桑田采桑缫丝,然后行祭祀蚕神大典。
世人笃信“天人感应”,认为先蚕礼能否成功举办与皇后德行有关,故先蚕礼之于皇后是一等一的大事。
今年天公不作美,忽冷忽热时旱时涝,先是早春一场霜雪将桑树冻死大半,待补栽完毕又遇大旱,生生将先蚕礼拖到清明以后,成了夏蚕礼。
“皇后礼服的一应浆洗晾晒我都亲力亲为,不敢假手他人。那日,我将洗净叠好的礼服亲自送到椒房殿,陈尚衣当着我的面打开细细查看,却在裙脚处发现一点灰色印渍,便一口咬定我用心歹毒,目的是让皇后不能如期举办先蚕礼。”七竹继续道,语气透着悲凉。
青绿追问:“这其中的过程便只有你一人经手么?”
七竹不假思索道:“我事后回想此事,礼服不在我手上仅有一次,我准备将礼服送椒房殿之时,因要小解,不能将礼服带进恭房,便交给随我一同去椒房殿的浣衣室宫人夏秋,还叮嘱她不能让旁人接触。若是别有用心的人搞鬼,便只有这一机会。”
青绿若有所思,沉吟道:“夏秋。”
七竹继续道:“我看了礼服上的印渍,是可以洗去的,便对陈尚衣说我拿回去再洗一遍,她却说‘再让你洗,我们都得掉脑袋’,不容我分辨,将我下了永巷。”言罢低头,默默叹了一口气。
青绿开门探头看了一下,转头继续问:“你可曾与浣衣室现任管事汪氏有过过节?”
七竹摇头:“不曾。”抬头看向青绿,似乎在判断青绿问这话何意。
青绿清澈的眼眸甚为关切地看着她。
七竹一顿,加快语速道:“我是骆越族人,男人是南境军队的戍卒,被南越王裹胁谋反,兵败后被杀,我被没入掖庭,在浣衣室干粗活,一直小心谨慎勤勉,得以升任浣衣室主管。”
七竹喘了一口气,继续道:“浣衣室的宫人大多是犯人眷属,我待她们甚好,多年来相安无事,直至前段时日汪氏来了,号称与椒房殿有关系,说话办事颇为颐指气使,我也不与她计较,只是更加小心谨慎。”
青绿点头道:“明白了。七竹嬷嬷,我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