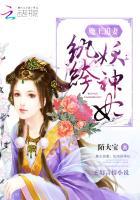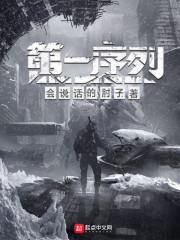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虎贲郎 > 第717章 主簿仲达(第2页)
第717章 主簿仲达(第2页)
某日深夜,赵基正在灯下批阅军报,忽闻门外喧哗。亲卫押来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自称是从洛阳逃出的旧吏,有紧急密情禀报。
那人跪地泣诉:“将军……司徒王允虽已被诛,然朝中仍有大臣忌惮您掌兵日久,威震北疆。近来有人暗中串联,欲奏请天子召您回京述职,实则夺其兵权,软禁于许都!”
赵基听罢,面色不变,只淡淡问道:“谁主使?”
“据闻是尚书令荀?幕中一名记室参军,与河内世家勾结,已写好奏章草稿,只待时机呈递。”
诸葛瑾闻讯赶来,忧心忡忡:“若天子真下诏,将军抗命则是逆臣,奉诏则是自投罗网。此局甚险。”
赵基沉默良久,忽而一笑:“他们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我不是靠洛阳的任命才站在这里的。我是靠着三百多个赎罪营兄弟的尸体,一百四十个雪耻营残生者的血,还有千千万万愿意相信我的边民,才走到今天。”
翌日清晨,他召集全体将领于校场誓师。
五千将士列阵如林,旌旗猎猎。赵基立于高台,声如洪钟:
“今日召诸君至此,并非为战,而是为誓!我赵基在此立誓:终我一生,绝不南下争权,绝不背叛北疆百姓!只要我还活着一天,阴山之南,便是汉土!胡马不得南牧,寇贼不得西侵!若有违此誓,天地共殛!”
全场肃然,继而爆发出震天呐喊:“誓死追随将军!誓守北疆!”
声浪滚滚,直冲云霄。
数日后,赵基派人将一封亲笔信送往许都,交予天子亲览。信中不提政事,不言兵权,唯述边情民生,附图三幅:一为新筑烽燧布局,二为屯田收成统计,三为阵亡将士名录。
末尾写道:“臣之所治,并非疆域,而是人心。愿陛下知边将之苦,悯士卒之劳,勿以猜忌伤忠良之心。臣虽远在寒陲,然每夜望星,皆思社稷安危。若天下太平,请记得是我们一起守住的。”
据说天子读罢,久久不语,终将信收入紫檀匣中,置于案头常观。
自此,再无人敢提“召赵基回京”之事。
岁月流转,十年如梭。
昔日的少年李昭已成长为忠烈营左曲都尉,脸上刀痕纵横,眼神坚毅如铁。他在一次巡逻中擒获两名冒充商旅的鲜卑细作,审讯得知,草原各部正秘密筹备联盟,意图联合南侵。
赵基闻讯,未惊未怒,只是召集全军将士,再度打开那本厚厚的名册??上面记录着每一位曾为国捐躯者的姓名。
他对众人说:“敌人以为我们会老,会倦,会忘记。但他们不知道,每一代人都会有新的张猛、新的李昭、新的雪耻营战士站出来。只要这块土地还有人愿意为之流血,那就永远不会陷落。”
于是,在那个风雪交加的冬夜,赵基再次亲率大军出击。这一次,不再是五百罪人组成的雪耻营,而是整整两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边防劲旅。
他们在参合陂旧战场附近设伏,利用地形诱敌深入。当鲜卑主力骑兵踏入埋伏圈时,万箭齐发,地雷骤响(由工匠仿古法所制,以火药引爆坑道),敌军阵型大乱。赵基亲执长戟冲锋,一举击溃联军中枢。
此战斩首一万三千余级,俘获首领三人,迫使草原各部重新签订盟约,承诺三十年内不得南侵。
战后,赵基并未举行庆功宴。他独自一人来到碑林,在第一批赎罪营的石碑前伫立良久。
风吹碑面,砂石轻响,仿佛有人低声唤他名字。
他知道,那是亡魂在低语。
也是信念在传承。
多年以后,当那位接过父亲军牌的少年穿上铠甲,成为新一代虎贲郎统领时,他曾站在晋阳城头问身边老兵:“为什么我们非要守在这里?明明南方富庶,京城繁华,为何要留在这个风沙满面的地方?”
老兵指着远方的地平线,淡淡地说:“因为你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有人用命换来的。你不守,谁守?”
少年默然,抬头望天。
夕阳西下,染红了整片碑林。
那里刻着无数名字,有些清晰,有些模糊,有些已被风雨侵蚀殆尽。
但它们曾经存在过。
就像那些跪过、痛过、哭过、最后选择站起来战斗的人一样。
真实地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