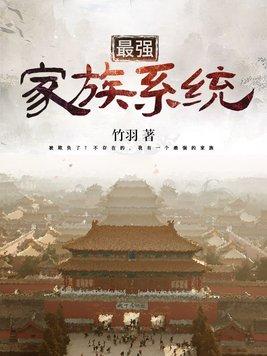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大火收汁短篇集 > 第3章 古板大伯哥x乡下粗蛮女主(第1页)
第3章 古板大伯哥x乡下粗蛮女主(第1页)
容家的天井,落满槐花。
容重云坐在厅内,烛火未燃,屋中清冷如井。祖母让他来接人,说是二弟容轻言成亲,新妇从乡下入门,需有长子作主引她入族谱。
他没拒绝。
对他来说,这只是又一场礼仪。
直到她走进来。
她穿着大红嫁衣,脚步稳,肩背挺,和那些垂头顺眼、眼波带怯的女子都不一样。
她一进门就先笑了,眼睛亮得像阳光下的水,眉眼张扬,带着一点粗气的野味。
“您是……容大公子?”她开口嗓音脆亮,语气里不见拘谨,反而像跟谁打趣,“轻言说您是这宅子里最正经的人,果然一脸凶相。”
容重云抬眼看她,那一眼落在她脖颈微敞的位置。
红衣衬得她皮肤发亮,发丝湿着一缕,贴在颈窝。他本能想移开眼,却移不开。
他只点头:“我是容重云。”
“我是游采薇。”她笑着向他伸出手,那动作像是和人拍肩打招呼,“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啦,大伯哥。”
那句“大伯哥”叫得太随意,太近,叫得他指节一紧,手里的书页被他掐皱一角。
她却还没察觉,笑着凑近:“我是不是冒犯了?我没啥规矩,您见谅。”
她身上有草木的味道,还有一点汗湿过的香,活生生的,热腾腾的,像是一团火,正对着他胸口贴近。
他一动不动。
他看见她唇角扬着,牙齿白,眼中无畏。他看得太久了,以至于她扬眉问了一句:
“大伯哥,你一直盯我,是不是我脸上沾了什么?”
容重云收回眼,唇线紧抿。
他不该看。
她是他弟的妻子,是容家的少奶奶,是来做主妇的,不是来让他——
他喉结轻轻滚动一下,像是强行咽下了什么。
“无事。”他低声说,转身,“时辰快到了,你去堂前候礼。”
她点头,迈步从他身边走过时,裙摆扫过他衣角,他闻见她身上那股热气又甜又冲。
那一瞬间,他胸口泛起一阵钝痛。
像被什么钝器敲了一下,不响,却闷得透不过气。
她走远后,他站在原地,指腹摩挲那道皱起的书页。
他不是没见过女子。
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叫他一眼就心乱,一声“家人”就让他想退却,又想靠近。
她太鲜了。
鲜得像春天刚拔节的草,像炭火上的酒,带着热、着了火,明明知道不能靠近,他却想尝一口。
只是尝一口,就好。
那日之后,容重云夜夜失眠。不是因为政务,不是因为宅务。
是因为他脑子里总是反复响着她那声:
“大伯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