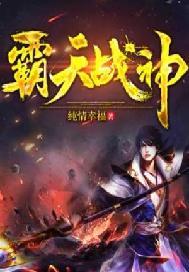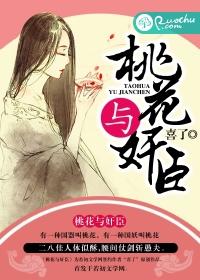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边关兵王: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1页)
第465章 燕返无踪(第1页)
周苍深吸一口气,茶水的热气模糊了他瞬间阴沉的面容。
他自然知晓,对方所言句句属实,而最让他忧心的是,东疆主帅林远图乃是二弟的人,这也是他入主东宫,登上太子之位最大的阻碍。
周苍沉默了良久,烛火在他脸上投下摇曳的阴影。他再次开口时,声音带着几分沙哑:“那先生要什么条件?”
那中年男子眼神中闪过一丝宛如饿狼般的贪婪,语气却依然平淡:“我们可以助你坐上太子之位,甚至可以扶着你登上皇位,但你要把东海沿岸。。。。。。
春雷未响,山野仍裹着残冬的寒意。守诺书院后山的蓝莲花还未破土,只在向阳坡上露出几点嫩芽,像是大地悄悄睁开的眼睛。晨雾弥漫,书院钟声穿过林梢,惊起一群宿鸟,扑棱棱飞向天际。新一批学子正列队于正殿前,准备参加入院仪式。他们大多来自边陲小县,衣衫朴素,眼神却亮得惊人,仿佛早已听过那幅巨画背后的故事,心中早埋了火种。
领头的是个瘦高少年,名叫陆沉,来自西南瘴疠之地。他父亲曾是驿卒,在一次雪崩中为护粮车坠崖而亡,临终前只留下半块刻有“路通归语”的木牌。母亲将木牌缝进他的里衣,送他北上求学,只说一句:“若你真想明白他为何非走不可,就去守诺书院看看。”
此刻,陆沉仰望着殿中那幅巨画,手不自觉地抚过胸口??木牌还在,贴着心口的位置微微发烫。他身旁的女孩叫柳穗,是北境寒脊关戍边校尉之女。她幼时曾随父走过那段被雪掩埋又被重修的古道,亲眼见过碑上“还在”二字。她记得父亲跪在碑前磕头的模样,也记得那一夜风雪中,全军齐声背诵院训的声音如何穿透寒夜。
主祭官由书院现任山长担任,正是当年小石头亲授《凡人志》的弟子。她已年近五旬,两鬓微霜,但目光依旧锐利如刀。她缓步登上高台,身后两名学童捧着一只陶罐,正是当年埋藏《凡人志》的那只,如今已被取出,重新启用,象征传承不灭。
“今日你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成为英雄。”她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也不是为了青史留名。你们来此,只为学会一件事:**记住真实**。”
她打开陶罐,取出一卷新誊抄的《凡人志?拾叁》,封皮无题,仅盖一方朱印:“不虚一字”。
“这一卷,记录的是永和十五年秋,陈七最后一次带队巡查‘铁脊峡’的事。”她缓缓展开书页,声音低沉下来,“那时他已病重,咳血不止,却坚持亲自走完全程。途中遇暴雨,山洪暴发,桥断路毁。众人劝返,他说:‘我若回头,后面的人就会觉得,这条路可以停。可它不能。’”
台下一片寂静。
“他在泥水中跋涉七日,靠喝雨水、嚼草根撑着。最后一夜,宿在一处破庙里,梦见阿音站在门口,手里提着灯笼。他想喊她,却发不出声。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真的握着一根红绳,是他多年贴身收藏的,说是阿音缝袍子时用剩的。”
陆沉听得呼吸微滞。
“第二天清晨,他没能站起来。”山长顿了顿,眼中泛起水光,“队员们抬着他往回走,三天后才赶到最近的驿站。医者说,肺腑尽腐,能撑这么久,全凭一口气。”
“那一口气是什么?”柳穗忍不住轻声问。
山长望向她,嘴角微扬:“他自己写的答案??‘怕后来人走到这里,发现没人替他们记下这条路有多难走。’”
话音落下,全场肃立。风吹动殿前蓝布幡,猎猎作响,宛如回应。
仪式结束后,新生们被分派至各习堂研读典籍。陆沉与柳穗同入“记事阁”,专攻《守路日记》系列整理工作。阁内藏书浩繁,自《拾贰》之后,又有三本陆续送达,皆由匿名之人寄来,笔迹不同,内容却一脉相承:有人记录某段荒废古道如何被牧民自发重修;有人写下某位老工匠临终前口述的筑桥技艺;还有一篇,竟是出自一名盲女之手,她请人代笔,讲述自己如何凭着记忆复原了陈七曾说过的一句话:“石头冷,人心热。”
“这些都不是官方史册会记的东西。”柳穗翻着一页页泛黄纸张,低声感慨,“可它们比任何金书玉牒都更像历史。”
陆沉点头:“因为这是活人的历史。”
夜里,两人留在阁中抄录,烛火摇曳。窗外忽传来??声响,似有人踏雪而来。陆沉推窗查看,只见庭院中央站着一位老者,披着灰褐色斗篷,肩扛铁铲,脚穿草鞋,鞋底沾满黄泥与碎石。他不说话,只是将手中一个油布包放在石阶上,转身离去,脚步无声,如同融入夜色。
陆沉追出,却不见踪影。
油布包里是一本全新日记,封面墨书四字:《守路日记?拾陆》。扉页写着一行小字:
>“我不是李守,但我走过他曾走过的每一步。
>这条路,不该只有一个人走。”
次日清晨,山长看到这本日记时,久久伫立,最终命人将其供于正殿画下,并召集全体师生宣读其中第一篇。
那是一段关于“哑岭”的记载。
永和十七年冬,朝廷终于下旨重修西北驿道,任命新任督工大臣主持其事。然而此人贪墨成性,只拨劣材薄款,强征民夫,逼迫百姓以血肉之躯填壑架桥。不到半年,死伤数百,怨声载道。消息传至归语村时,陈七已卧床不起,听闻此事,竟挣扎起身,写下一封信,托人送往长安。
信中只有一句: